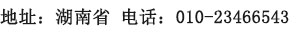辽太祖、太宗时期,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世宗至圣宗前期,除秋捺钵地大体呈西移趋势之外,其他三季捺钵地皆南移,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基本呈南-北走向。圣宗后期至辽末,春捺钵北移至松嫩合流处诸湖泊,冬捺钵多在永州广平淀,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变为东北-西南走向。
捺钵为有辽一代重要制度,向来受学界重视。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池内宏已撰文研究,美国学者魏特夫、冯家升的著作中也有所涉及,上个世纪40年代,傅乐焕对捺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释。近年来,相关论著更是层出不穷。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谈一点对捺钵地变迁的新思考,以求正于史界方家。
一
纵观辽代诸帝捺钵地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即太祖、太宗时期;中期,世宗、穆宗、景宗至圣宗前期;后期,圣宗后期至兴宗、道宗和天祚时期。
《武经总要》前集卷22《番界有名山川·木叶山》、《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资治通鉴》卷引《虏庭杂记》、《辽史》卷《国语解》,以及《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 等书皆记载:“太祖四季常游猎于四楼之间。”傅乐焕认为,“四楼”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四时捺钵之地。考之《辽史》卷37《地理志》,祖州“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降圣州“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东楼、西楼确为阿保机春秋捺钵之地,前者指降圣州,后者指祖州。需要说明的是,上京、祖州同号西楼,阿保机秋捺钵地最初在上京,后因上京汉城发展,逐渐成为农业和贸易的中心,不便于游牧射猎,阿保机秋季才常驻祖州附近。
阿保机夏捺钵地北楼的所在地史书记载不一。《资治通鉴》卷引《虏庭杂记》称在阿保机所部“北三百里”,《武经总要》前集卷22《番界有名山川》称在木叶山北,《辽史》卷《国语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皆称在唐州。唐州《辽史》无载,见《契丹国志》卷22《诸藩臣投下州二十三处》,冯永谦推测,“可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或巴林左旗的北部”,则唐州正在后来的庆州境内。亦有学者推测北楼在辽庆州北境黑山。若是,称阿保机夏捺钵在唐州、在庆州皆指同一地域。《辽史》卷2《太祖纪》,天赞四年“五月甲寅,清暑室韦北陉。秋九月癸巳,至自西征。”据《旧五代史》卷32《唐书·庄宗纪》,同光三年()六月癸亥,云州上言:“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阿保机西征自碛北返回,则其清暑之室韦北陉,必在辽庆州。陈汉章《辽史索隐》卷一“室韦北陉”注“此当是北楼”。由此看来,阿保机夏捺纳多在后代辽庆州域内,其地亦称室韦北陉。
阿保机称可汗之七年,“秋八月己卯,幸龙眉宫”,“九月壬戌,上发自西楼。”“冬十月庚午,驻赤崖。”“十一月,祠木叶山。还次昭乌山”,“十二月戊子,燔柴于莲花泊。”据《辽史》卷37《地理志》,龙眉宫在上京,此处的西楼当指上京,是阿保机早年秋捺钵处,则此年十月以下的记载,正是阿保机赴冬捺钵的行程。据胡峤《陷辽记》,至仪坤州之后,“又二日,至赤崖”,贾敬颜认为:“赤崖必距上京不远,而在其西南方向”。应为确论。昭乌山,陈汉章认为“当在木叶山西南,或即今土默特左翼东南野狐山”。莲花泊,在“奉天府海城县西南六十里”。是阿保机自上京出发,于十一月抵达永州,祠木叶山后“还次昭乌山”,显然木叶山非其停驻之处,其冬捺钵不在木叶山附近的南楼,而在今辽宁海城的莲花泊。九年“冬十月戊申,钩鱼于鸭渌江”;神册三年“冬十二月庚子朔,幸辽阳故城”,皆可证阿保机冬捺钵在辽东半岛。
综上,阿保机秋捺钵在上京、祖州,由此东行经永州(木叶山)赴辽东半岛的冬捺钵地,春季由辽东半岛西行至降圣州春捺钵,再西行赴庆州夏捺钵。关于阿保机的四时捺钵,《辽史》详载春、秋捺钵地,对夏、冬捺钵地语焉不详,可能是契丹人最初更重视春水秋山的缘故。金代没有四时捺钵的概念,仅分春水秋山两个系列,或是契丹人古俗的体现。
太宗天显四年六月“癸亥,驻跸凉陉”,“八月辛丑,至自凉陉”,可见凉陉是太宗夏捺钵地。参之是年六月“己酉,西巡”,七月“甲午,祠太祖而东”,此凉陉在上京西,很可能即太祖夏捺钵的“室韦北陉”,笼统说,在辽庆州境。但是,从会同三年七月“猎于炭山”的记载来看,会同七年、八年、九年夏季太宗所赴凉陉应为炭山凉陉。炭山在今河北沽源、丰宁之间。太宗天显间和会同间之夏捺钵虽然皆称凉陉,但地点不同。
太宗也常“清暑沿柳湖”,天显五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辽史》皆有太宗赴沿柳湖的记载。天显五年六月“乙卯,如沿柳湖。丁巳,拜太祖御容于明殿”。据《辽史》卷37《地理志》祖州天成军条,“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乙卯与丁巳中间仅隔一日,可知沿柳湖在祖州附近。参之《辽史》卷37《地理志》怀州奉陵军:“太宗行帐放牧于此”,“有清凉殿,为行幸避暑之所。皆在州西二十里。”则沿柳湖应在怀州境。
此外,史书中至少还可以发现两处太宗夏季驻地。其一,会同二年,“是夏,驻跸频跸淀。”陈汉章认为即见于天显十年的品不里淀,所在地不详。其二,天显五年“五月戊辰,诏修褭潭离宫”。据胡峤《陷辽记》:“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又东行,至褭潭”。品其文意,褭潭应在上京东二日程。丁谦认为褭潭“当即大布苏图泊”。齐召南《水道提纲》卷27《塞北漠南诸水》:“阿禄科尔沁地有大布苏图鄂模”,《中国历史地图集》置大布苏图泊于哈喜尔河与乌里吉木伦河交汇处,约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与开鲁县交界处。贾敬颜认为褭潭为“今开鲁县西北之塔拉干泡子”,《中国历史地图集》从之。恐皆失之过东。概言之,太宗虽继承太祖于庆州诸山夏捺钵的习惯,但夏季也常驻上京与祖州附近,即太祖秋捺钵地。
天显三年“二月,幸长泊”,应为太宗春捺钵地。长泊所在地学者看法不一,傅乐焕认为在今内蒙古奈曼旗境的工程庙泡子(一名乌兰浪泡),王守春认为大致位于今奈曼旗西稍北约10至20公里处,胡廷荣认为在今敖汉旗木头营子乡中哈沙吐村南,孙冬虎认为在今敖汉旗长胜乡西梁村附近。诸说虽不同,皆不出今敖汉、奈曼二旗,按辽代行政区划,皆在降圣州境内。天显九年正月、十一年正月、会同二年十二月、九年三月,皆见太宗钩鱼于土河的记载,应是降圣州境内的老哈河水域。可证太宗继承了太祖的春捺钵地。
天显三年“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升东平郡为南京”,此后太宗冬季经常驻南京(今辽宁辽阳)。天显四年十二月“甲申,观渔三叉口。”三岔口在海城县西六十里,辽河、浑河、子河合流处,紧邻太祖冬捺钵的莲花泊。证明太宗冬驻南京既是出于控制东丹国的政治需要,也是对太祖冬捺钵地的继承。或许迁东丹民实东平,就是将东丹民迁入契丹冬捺钵地以便控制。
天显九年十二月“驻跸百湖之西南”,陈汉章《辽史索隐》卷一:“土默特二旗,辽为兴中府,治兴中县。百湖在左翼东六十里,蒙古名兆布拉克。”但是年八月“自将南伐”,归途中“十二月壬辰,皇子阿钵撒葛里生,皇后不豫”,次年“正月戊申,皇后崩于行在”,恐怕是行军途中因皇后产后病重而临时留驻,非常规的冬捺钵地。
概言之,太宗四时捺钵地基本与太祖相同,只不过其夏季也常在太祖秋捺钵处,冬季多驻南京(今辽宁辽阳)。夏秋同在一处,正是将夏捺钵并入“秋山”故俗的体现。会同年间新开夏捺钵地炭山凉陉,成为后世诸帝夏捺钵常驻之处。
二
世宗天禄二年“十一月,驻跸彰武南。”《辽史》卷39《地理志》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有大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世宗尊号天授皇帝,能留下刻石,自非普通驻地,麝香崖、驻龙峪一带,应为世宗冬捺钵地。天禄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陈汉章认为即太宗曾驻跸之兴中府百湖。可证世宗冬、春捺钵皆在兴中府,是将太宗偶然驻跸之所变成了捺钵地。冬春皆在一地,正是将冬捺钵并入“春水”故俗的体现。
世宗夏捺钵的记载,仅见天禄五年,“是夏,清暑百泉岭。”陈汉章认为即“札鲁特左翼西南车尔百泉冈”。若是,则世宗的四时捺钵地与太祖、太宗完全不同,其四时迁徙也由太祖、太宗时的东南-西北方向,变为正南-正北方向。世宗在位虽然仅4年,资料也很残缺,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太祖、太宗旧捺钵地之外确立新捺钵地的趋势。但是,至世宗时还保持着“春水秋山”的旧俗,即将冬捺钵并入“春水”,将夏捺钵并入“秋山”。
穆宗即位之初行踪不定。应历二年九月“猎炭山”,十二月“猎于近郊”,三年三月“如应州击鞠”,“观渔于神德湖”,“是冬,驻跸奉圣州”,四年二月“幸南京”(析津府),十二月“谒祖陵”,“是冬,驻跸杏堝”,五年二月“如褭潭”。神德湖在辽应州浑源县,可见,应历三年穆宗春捺钵在应州,冬捺钵在奉圣州。《辽史》卷40《地理志》南京析津府漷阴县:“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应历四年二月穆宗“幸南京”可能与此有关,即是年穆宗春捺钵可能在延芳淀。杏堝,《辽史》卷39《地理志》中京大定府武安州:“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有黄柏岭、袅罗水、个没里水。”第一个“水”字衍,应为“袅罗个没里水”,即潢河。圣宗时始建武安州杏堝新城,此前的杏堝在木叶山下,临潢河,此即应历四年穆宗冬捺钵地。以上所考各处此前皆未曾作为捺钵地。穆宗亦赴此前已确立的捺钵地,但其前往的时间与从前不同。上京、祖州自太祖时起为秋捺钵地,而穆宗猎于上京近郊和赴祖州谒祖陵却皆在十二月;炭山、褭潭为夏捺钵地,而穆宗却于深秋九月猎炭山,于仲春二月如褭潭。综上可见,穆宗试图抛开太祖、太宗旧俗,确立新的四时捺钵地。
应历七年二月“驻跸潢河”,此后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八年皆有类似记载。应历十三年二月“壬辰,如潢河”,“三月癸丑朔,杀鹿人弥里吉”,“夏四月壬寅朔,猎于潢河。”十八年“三月甲申朔,如潢河。乙酉,获驾鹅,祭天地。”据此,穆宗春捺钵之潢河段,应有水淀,有天鹅,附近有山林可以猎鹿。其地最可能是穆宗应历四年去过的靠近潢河和木叶山的杏堝。笼统而言,穆宗应历七年以后的春捺钵之地,基本是在永州境内。应历十五年二月“上东幸。甲寅,以获鸭,除鹰坊刺面、腰斩之刑……(三月)癸巳,虞人沙剌迭侦鹅失期”,十六年“三月己巳,东幸。庚午获鸭,甲申获鹅”。此东幸之地应即穆宗春捺钵驻跸潢河之地。据《辽史》卷68《游幸表》,应历十年二月、十八年二月皆“如褭潭”,这是穆宗另一处春捺钵地。
应历九年六月“如怀州”,十年五月“谒怀陵”,“八月,如秋山,幸怀州。”十七年“是夏,驻跸褭潭。”十八年“是夏,清暑褭潭。”证明穆宗夏季常在怀州避暑,是继承了其父太宗的夏捺钵地,偶尔秋季也在怀州。值得注意的是,穆宗既“清暑褭潭”,也在春季驻褭潭,春夏捺钵地相同,打破了“春水秋山”中冬春捺钵同处、夏秋捺钵同处的旧俗,开始了向四季捺钵地截然分开的过渡。
《辽史》卷37《地理志》庆州玄宁军:“有黑山、赤山、太保山”。应历十二年“秋,如黑山、赤山射鹿”,此后庆州诸山成为穆宗秋捺钵地。应历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冬皆“驻跸黑山平淀”,十八年冬“驻跸黑山东川”,证明穆宗后期庆州诸山亦是其冬捺钵地。据《辽史》卷68《游幸表》,应历七年十二月“猎于赤山。猎于拽剌山。”十三年“秋,射鹿于黑山、拽剌山。”证明拽剌山与赤山、黑山相邻,亦在庆州境内。参之《辽史》卷6《穆宗纪》,应历八年七月“猎于拽剌山”,可证穆宗赴庆州冬捺钵始见于应历七年,赴庆州秋捺钵始见于应历八年。
经过即位初年的尝试之后,约自应历七年起,穆宗春捺钵多在永州,夏捺钵常在怀州或褭潭,秋冬捺钵皆在庆州诸山。夏捺钵地继承了太宗时的传统,冬捺钵也与太祖、太宗冬捺钵地在同一区域,只不过其驻在、游猎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春秋捺钵地则与此前诸帝不同。
景宗保宁二年“春正月丁未,如潢河。”三年“十月癸酉,东幸。”五年正月“如神得湖。如应州。”此神得湖,即上文提到的神德湖。六年“春正月癸未,幸南京。”乾亨二年闰月“如南京赏牡丹”,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幸。己丑,复幸南京。”皆为穆宗春捺钵旧地。仅保宁十年“春正月癸丑,如长泊”,是太宗春捺钵旧地。可证景宗春捺钵地基本是沿袭了穆宗的传统。
景宗夏季驻地多变,见于《辽史》记载的有燕子城(3次)、沿柳湖(2次)、冰井(2次)、频跸淀(1次)、惠民湖(1次)、羊城泊(1次)等处。燕子城即今河北张北县旧城,冰井也在今张北县境内,羊城泊在今河北沽源县北,皆属辽奉圣州,此前未做过捺钵地。沿柳湖、频跸淀为太宗夏捺钵旧地。惠民湖,据《辽史》卷37《地理志》上京道记载,上京道有兴国惠民湖,庆州又有兴国湖,则兴国湖、兴国惠民湖、惠民湖三名应指同一湖,或相距很近的两个湖,位于庆州附近,即在太祖、太宗夏捺钵之区域内。《辽史》卷41《地理志》奉圣州所属归化州:有“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承天皇后纳凉于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于此”。可证景宗另一处重要的夏捺钵地在西京奉圣州。
景宗保宁三年九月“甲寅,如南京”,六年七月“庚申,猎于平地松林”,八年九月至怀州“谒怀陵”。自保宁十年八月始见“猎于赤山”,证明景宗秋捺钵在庆州诸山是保宁十年以后的事。乾亨三年八月、四年九月皆“猎于炭山”,说明其以炭山为秋捺钵地更晚一些。
景宗的冬捺钵,保宁三年“是冬,驻跸金川。”四年“冬十月丁亥朔,如南京。”五年“冬十月丁酉,如南京。”十二月“如归化州”。六年“冬十月乙亥朔,还上京。”七年“冬十月,钩鱼土河。”八年十月“如长泊”。九年十月“如老翁川。钩鱼于赤山泊。”十年“是冬,驻跸金川。”乾亨元年“是冬,驻跸南京。”二年十月“次南京”。可见,景宗冬捺钵较多是在南京。除南京外,仅金川出现两次。保宁三年,《辽史》卷8《景宗纪》称“是冬,驻跸金川”,卷68《游幸表》十月条称“驻跸于蒲瑰坂”,两地应相邻。《游幸表》载是年九月景宗“猎于胡土白山”,即《金史》卷24《地理志》西京抚州境内的麻达葛山,在辽奉圣州境,则金川、蒲瑰坂皆应在辽西京奉圣州。概言之,景宗冬捺钵地虽存在变化,但更多是在南京和西京境内,而不是傅乐焕所说的上京、西京。
综上,景宗四时捺钵地虽然较富变化,但大体是对太宗旧制的继承,只不过将冬捺钵由原来辽东半岛的旧南京东平郡(今辽宁辽阳),即后来的东京,转到新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景宗时捺钵地的最大变化是四时皆曾赴西京奉圣州及应州。据《辽史》卷41《地理志》奉圣州望云县:“景宗于此建潜邸,因而成井肆。穆宗崩,景宗入绍国统,号御庄。后置望云县,直隶彰愍宫,附庸于此。”当是景宗即位前曾生活于此的缘故。
三
圣宗统和四年三月对宋亲征以前,春季皆赴长泊,夏季皆赴木叶山并返回上京,秋季或在祖州、庆州,或东幸显州、乾州,冬季则在显、乾一带。由此分析,圣宗初年很可能是要恢复太宗的捺钵地。统和四年至统和七年正月班师以前,圣宗一直在南京境内,但此为战时状态。统和八年至十年春皆在台湖、沈子泊,在上京附近,或赴南京、炭山,夏驻炭山清暑,秋季仍驻清暑地,冬季,统和八年十月“驻跸大王川”,所在地不详;十年“十二月庚辰,猎儒州东川”,儒州在今北京延庆,即辽南京析津府附近。大体说,此时圣宗的四时捺钵是来往于上京、南京之间。
统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春夏捺钵地相当固定。春,延芳淀、鸳鸯泊,二十年以前基本在延芳淀,以后基本在鸳鸯泊,可以肯定的例外仅有十一年在褭潭、十六年在长泊。夏,偶尔有赴上京、南京或木叶山的记载,但每年皆清暑炭山。秋季驻地见平地松林、饶州、得胜口、南京、黑河、显州、女河汤泉、犬牙山等地。平地松林在潢河发源地,饶州在今内蒙古林西县,位于潢河上游,得胜口为今河北廊坊东南76里得胜口乡,黑河在辽庆州,显州在今辽宁北镇西5里北镇庙,女河汤泉在今辽宁锦州境,犬牙山在今河北赤城北。冬季驻地见蒲瑰坂、可汗州、驼山、南京、显州、七渡河及中京。驼山在今三河县,七渡河在今昌平境,可汗州在今河北怀来。大体说,此时期圣宗的秋捺钵在潢河上游、大凌河下游,以及南京、奉圣州一带,冬捺钵基本在南京及奉圣州。
统和二十六年至太平元年的捺钵地比较杂乱,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春季是萨堤泊(4次),夏季是永安山(4次),秋季是庆州诸山(5次),冬季是中京(6次),但并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寻。
太平“二年春正月,如纳水钩鱼。”纳水即今嫩江,此为赴松嫩合流处附近春捺钵之始。统和二十九年“冬十月庚子朔,驻跸广平淀。”此为赴广平淀冬捺钵之始。太平二年以后的春捺钵地,除六年的鸳鸯泊以外,纳水、长春州、鱼儿泊、挞鲁河(长春河)、混同江(鸭子河),皆在松嫩合流处一带,夏季皆在永安山,春夏捺钵地比较固定。秋季驻地见赤山、黑山、平地松林、辽河、中京、南京及附近地区,冬季驻地见上京、辽河、南京,规律性仍不明显。
综上,圣宗四时捺钵地大体可以统和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春捺钵延芳淀、鸳鸯泊,夏捺钵炭山,秋捺钵潢河上游和大凌河下游,冬捺钵南京及奉圣州。后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探索,至太平二年以后,春捺钵在松嫩合流处诸湖泊,夏捺钵永安山,秋捺钵以庆州诸山、平地松林为主,冬捺钵以南京附近为主。
兴宗春、夏、秋捺钵地皆是对圣宗的继承,冬捺钵基本是在中会川,即广平淀,其次则为中京。
道宗春、秋、冬捺钵地皆是对兴宗的继承。只是冬季也常驻南京,秋捺钵可能比较重视永州伏虎林。《辽史》卷32《营卫志》:“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慄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辽史》载道宗清宁二年“八月辛未,如秋山”,《焚椒录》作清宁“二年八月,上猎秋山,后率妃嫔从行在所,至伏虎林”。证景宗至道宗初,永州伏虎林一直是秋捺钵地。
清宁五年“夏六月甲子朔,驻跸纳葛泊。”清宁八年“六月丙子朔,驻跸拖古烈。”此后,夏捺钵以此两地为主。据傅乐焕统计,道宗夏月赴拖古烈10次、纳葛泊9次、散水原6次、庆州4次、赤勒岭4次、永安山4次、撒里乃3次、犊山2次、炭山2次、黑岭2次。拖古烈为蒙古语“牛犊”的音译,意译为“犊山”,即《辽史》卷32《营卫志》所载夏捺钵地“吐儿山”(今兔儿山),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作“犊儿山”。与永安山、黑岭皆属庆州。纳葛泊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撒里乃,《金史》卷24《地理志》北京路临潢府:“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统九年尝避暑于此”,可知两地皆在辽上京。上面统计的道宗夏捺钵地可考者36次,在庆州诸山计22次,在上京12次,在炭山2次,显然是以庆州诸山为主。
圣宗、兴宗夏捺钵皆在永安山,道宗多在吐儿山,据年出使辽朝至吐儿山的沈括记载:“近日北朝文字称,今年在永安山受礼,今来馆舍却去永安山八九十里”,两山相距约八九十里。由此看来,《辽史》卷32《营卫志》所载,春捺钵在鸭子河泊、夏捺钵“多在吐儿山”、秋捺钵“曰伏虎林”、冬捺钵“曰广平淀”,显然是道宗时事。夏捺钵下载:“道宗每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学界通常认为《营卫志》所载是圣宗以后的情况,恐怕是不正确的。
综上,圣宗后期始确立起春捺钵在松嫩合流处的诸湖泊、夏捺钵在永安山、秋捺钵在庆州诸山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兴宗又确立了冬捺钵在广平淀的传统,道宗、天祚基本是对此传统的遵循,只不过道宗将夏捺钵地改至距永安山八九十里的吐儿山。王易《重编燕北录》:“四时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千)[十]里就(烁)[泊]甸住坐,夏捺钵多于永安山住坐,秋捺钵多在靴甸住坐。”靴甸为广平淀别名,这说的显然是兴宗以后的情况。
辽代诸帝的捺钵地可以归纳如下表。
春捺钵
夏捺钵
秋捺钵
冬捺钵
太祖
降圣州
庆州黑山
上京、祖州
辽东半岛
太宗
庆州黑山,上京、祖州、怀州
世宗
霸州
今内蒙古札鲁特旗
霸州
穆宗
永州
怀州或褭潭
庆州诸山
景宗
降圣州,应州,南京
怀州,奉圣州,庆州
庆州诸山,炭山
南京、西京
圣宗
延芳淀、鸳鸯泊
炭山
潢河上游,大凌河下游
南京及奉圣州
松嫩合流处诸湖泊
永安山
庆州诸山,平地松林
南京
兴宗
广平淀
道宗
吐儿山
大体而言,有辽一代捺钵地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太祖、太宗时期,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中期,世宗至圣宗前期,除秋捺钵地大体呈西移趋势之外,其他三季捺钵地皆南移,西京奉圣州、应州诸山与湖泊,以及南京的延芳淀,成为冬春捺钵的主要地点,夏捺钵渐由怀州、庆州南移至炭山、奉圣州,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基本呈南-北走向。后期,圣宗后期至辽末,春捺钵北移至松嫩合流处诸湖泊,夏捺钵与前期在同一地理范围即庆州诸山,秋捺钵或与夏捺钵同地,或在平地松林及炭山,冬捺钵多在永州广平淀,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变为东北-西南走向。
傅乐焕将景宗以后的捺钵地分为两组。东北组,春在混同江、鱼儿泊,夏在永安山等地或在纳葛泊,秋在庆州诸山,冬在广平淀;西南组,春在鸳鸯泊,夏在炭山或纳葛泊,秋在炭山,冬在南京或西京。“自圣宗后半,历兴道两朝,以迄天祚初期,百有余年,大率盘桓东北组中。然每阅五,六年亦必至西南组一行。”实际上,圣宗统和二十五年以前几乎年年清暑炭山,而此后夏捺钵多在永安山,再也没有清暑炭山的记载,傅乐焕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其说仅就春捺钵立论,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四
由于随行捺钵的人畜较多,对草场质量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胡峤《陷辽记》提到,汤城淀“地气最温,契丹若大寒,则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软如茸,可藉以寝。”太宗夏捺钵地褭潭“始有柳,而水草丰美。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这两处都是捺钵地,可证捺钵地皆存在优质草场。《辽史》卷60《食货志》在记载辽代马政时提到:“祖宗旧制,……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四时捺钵竟然用马数万匹,即使我们保守地按1万匹计算,在捺钵地驻扎一个月,放牧这些马就至少需要60多万亩优质草场,更何况还携有其他牲畜。即使捺钵的队伍可能携带部分饲料,其他牲畜不会久养而是随时杀食,能够驻扎一个月左右的捺钵地也必须有60万亩以上的优质草场,再加上其中肯定存在的湖泊、湿地或沙地等不适宜放牧的区域,能够驻扎一个月的捺钵地应至少占地平方公里以上。换言之,随皇帝捺钵的所有人员不可能集中驻扎,从理论上讲,是分散在直径20公里左右的圆形区域内,或边长20公里左右的方形区域内。圣宗以后的春捺钵地,“鸭子河泊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冬捺钵地广平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都是符合这一条件的。《辽史》记载的许多驻地出现频率较低,且地名生僻,所在地无考,可能都是自然条件不足以久驻的偶尔停留之所,或是途经之地。
存在60万亩以上优质草场,是成为捺钵地的先决条件,在优质草场逐渐被开垦为农田之后,捺钵地的选择不得不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靠近农耕地区以就近获得物资供应,一是远行寻找新的优质草场,南部捺钵地的变化主要体现前者,北部捺钵地的变化主要体现后者。概言之,捺钵地的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经常捺钵的地区还存在着过渡开发、自然环境受到破坏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是圣宗以后的冬捺钵所在地广平淀附近。广平淀也名白马淀,原名柳林淀。北宋在11世纪40年代编撰的《武经总要》前集卷22《北蕃地理》记载:“白马淀,秦起塞,西自临洮,北临沙漠,即此也。”这时的广平淀还只是“北临沙漠”;《辽史》卷32《营卫志》冬捺钵条:“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至辽末,这里已经是“四望皆沙碛”了。年出使辽朝的宋绶记载:“至香山子馆,前倚土山,依小河,其东北三十里即长泊也。涉沙碛,过白马淀,九十里至水泊馆。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边平处,国主曾于此过冬。”宋绶也注意到了当地的沙漠化情况,白马淀以南已经“涉沙碛”,可见至晚在11世纪20年代,当地的沙地已经开始南扩了。因此,元代修《辽史》时就评价道:“辽地半沙碛”。圣宗以后四时捺钵地多不在契丹故地,应与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有关。
由于契丹故地的优质草场或被开垦为农田,或因过渡开发受到破坏,适宜做捺钵地的草场越来越少,使四时捺钵地逐渐远离契丹故地,同时也就远离了政治中心五京,这无疑会使皇帝对国家政治的掌控力度削弱。辽圣宗以后,出现捺钵队伍驻扎在捺钵地而皇帝返回五京的现象,显然是应对此问题的新举措,但终辽之世,捺钵地对政治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却是一直存在的。
*该文刊于《安徽史学》年第2期,文字有改动,引用时请核对原文。
[作者简介:杨军,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成名,论文发表时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